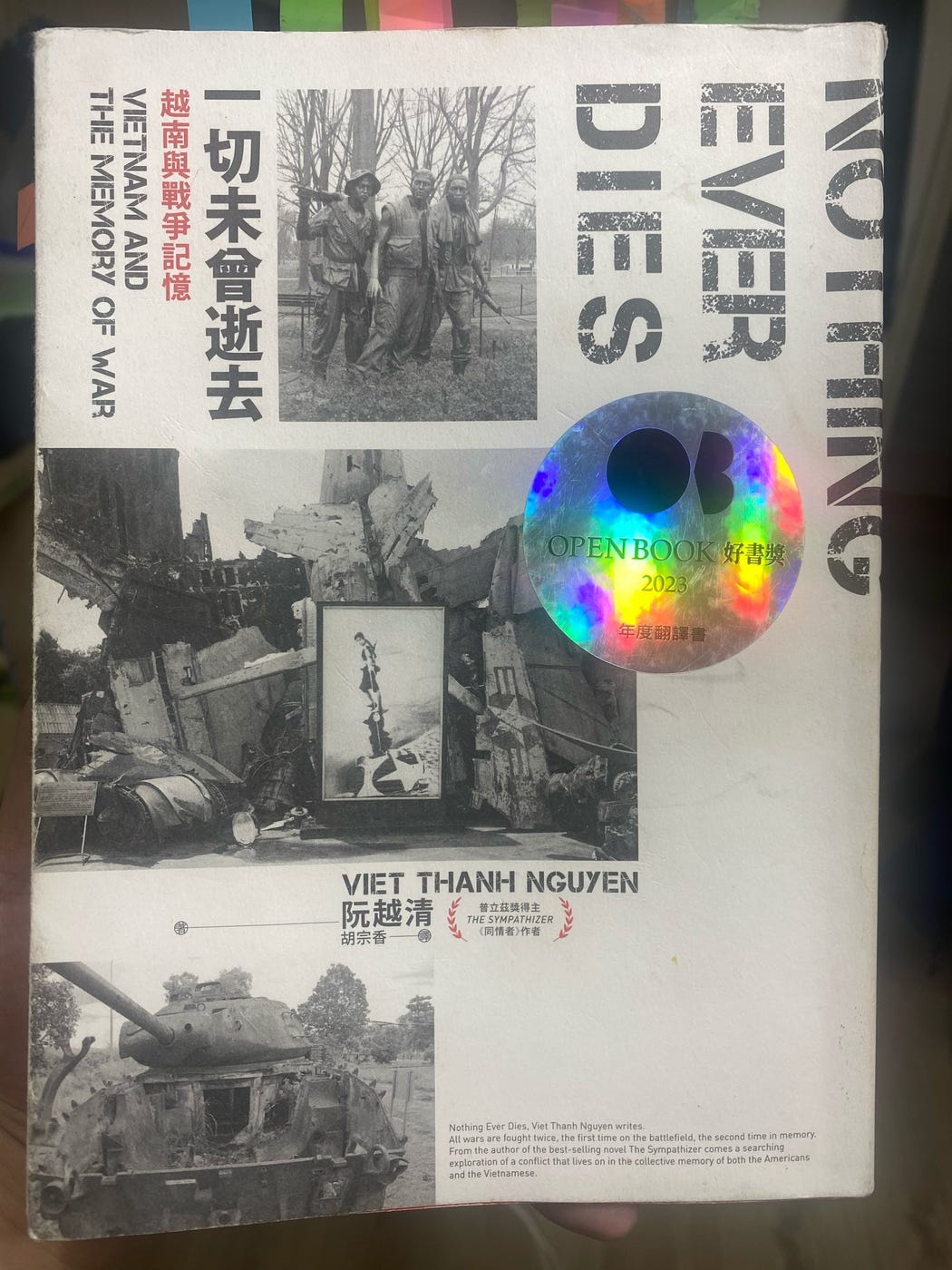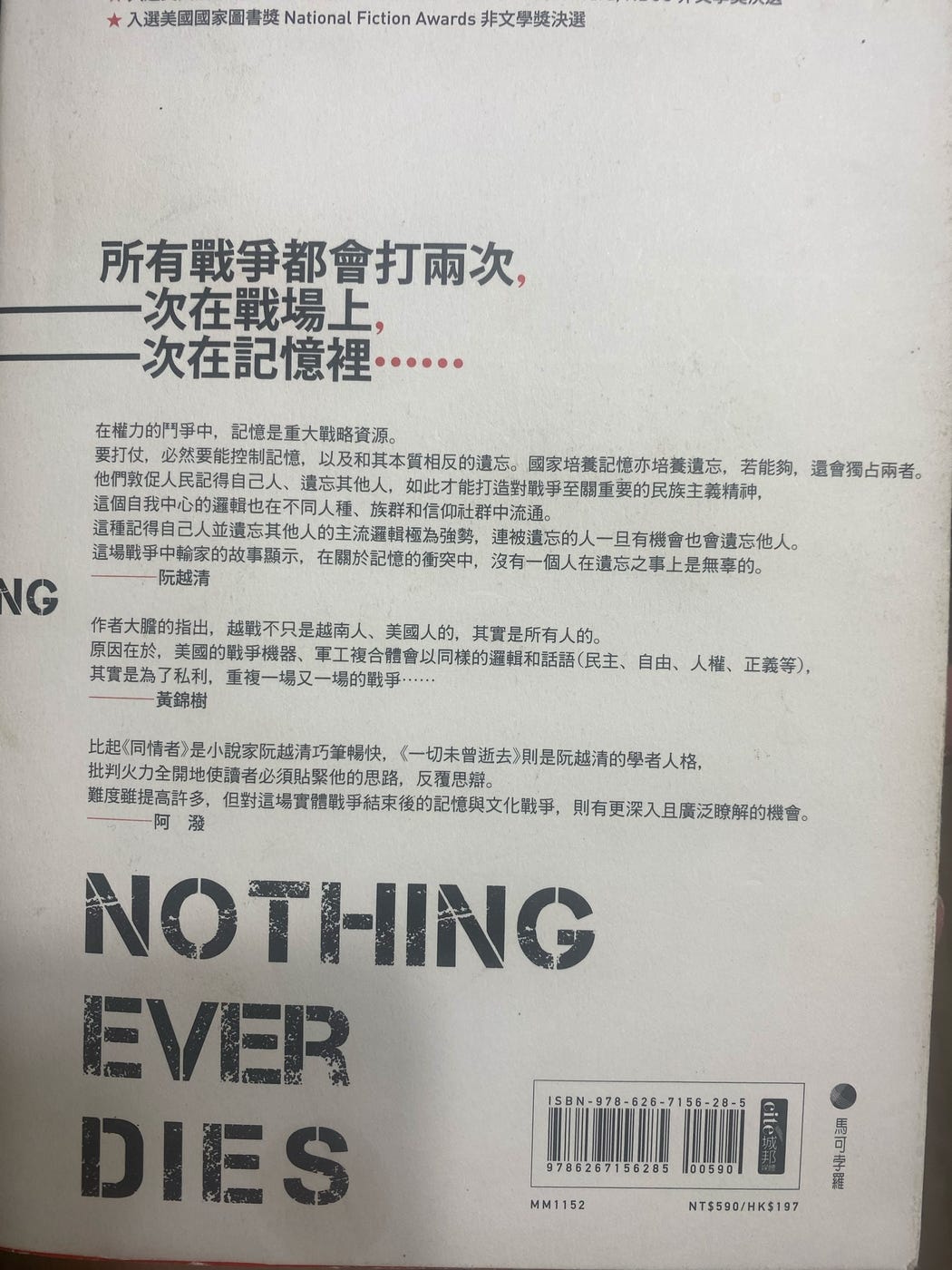「烏犬排練間」第一百一十四期:「你說的我不相信」
啊,原來記憶的戰場,也發生在我家的餐桌上!在餐桌的戰場邊,小脉緊張地縮在沙發上看卡通,而喝了點酒的我與父母大聲地爭執著。也因為我愛著父母、我父母也愛著我,所以竟然在爭執的最後有了第一個共識:「我們接受不同版本的故事是同時存在的。」
從去年推出戰爭首部曲《神去不了的世界》之後的好長一段時間,我和子玲都在探索「戰爭二部曲」的創作方向。首部曲在討論台灣二戰時期被塵封的台籍日本兵的記憶與世代創傷,那二部曲要延續下去的線索與切入角度會是什麼呢?
奇怪的是,我有一個直覺:需要先離開台灣的歷史,才能重新看見台灣。
於是,我跟子玲說:我們來研究「越戰」吧!
我沒有想到這個提議,竟然讓我們在接下來的半年裡,埋首在書海跟各種資料裡。然後像是著魔一般,幾乎每天都是讀書會。甚至連劇本都重寫了三個版本,直到今年過年從北越回來以後,才寫出讓我們都認同的故事!
「所有戰爭都會打兩次,一次在戰場上,一次在記憶裡⋯⋯」
— 阮越清
在所有書單裡,阮越清的《一切未曾逝去》是影響我們最大的一本書。阮越清是難民出身的越裔美國籍作家,他的小說《同情者》獲普立茲獎,而這本《一切未曾逝去》則是討論著記憶的倫理。
真實的戰爭裡,只有「戰勝」、「戰敗」、「和局」三種結果。但是在戰爭過後,不同的陣營會持續地進行「意識形態與文化的戰場」,目的是重新改寫人們對於戰爭的記憶。重新書寫人民對戰爭的記憶,是掌權者重要的戰略資源。只是,對於曾經發生過的悲劇,什麼才是真實的?什麼才叫做「公正」(或者說,「正義」)?
戰爭二部曲:《你說的我不相信》
這部作品的劇名來由很直接,純粹是我發現自己對台灣的記憶和父母親對台灣的記憶完全不一樣!
就在今年小年夜的餐桌上,我和父母在「戒嚴」這個議題上吵了起來!他們不覺得有過戒嚴、也不覺得戒嚴對生活有任何影響,有趣的是,真正經歷過戒嚴那年代的是他們!
所以,當我訴說著台灣史上曾經發生的一些重要事件,都被「我不相信你」一句話輕輕地帶過去。
啊,原來記憶的戰場,也發生在我家的餐桌上!在餐桌的戰場邊,小脉緊張地縮在沙發上看卡通,而喝了點酒的我與父母大聲地爭執著。也因為我愛著父母、我父母也愛著我,所以竟然在爭執的最後有了第一個共識:「我們接受不同版本的故事是同時存在的。」
原住民的歷史、國民黨軍隊的歷史、不同族群的歷史在同一個時間點上,是同時存在的,沒有誰的記憶可以取代誰。至少,我們先從尊重所有的記憶都是真實的作為起點。
沒有要去說服誰,只是讓所有關於「人」的故事同時存在。
很奇怪,我與父母的共識,讓我感受到一種溫柔。這份溫柔,讓我對台灣這片土地的情感有更深的聯繫。而在戰爭二部曲—「你說的我不相信」裡,我也想傳遞這份情感給觀眾。
雖然,在傳遞這份溫柔之前,得先經過一件悲劇事件:「金門三七事件」。
在這個以「三七事件」作為背景的故事裡,我沒有資格替這起事件做任何的註解。所以我儘可能的放大每一個人的角度,讓不同人的心思同時存在。
看這部戲會很需要歷史背景的知識嗎?我不知道。我盡可能地不要讓認知過程需要有預設知識的門檻,畢竟我真正在寫的是人心。看完這部戲會很難過嗎?我不知道。但我記得我書寫完劇本的那一刻,我流下眼淚,再次發現自己好愛台灣這片土地、好愛在台灣這座島嶼上所有的人。
期待與你劇場相見!
延伸閱讀:
:戰爭二部曲:《你說的我不相信》節目介紹